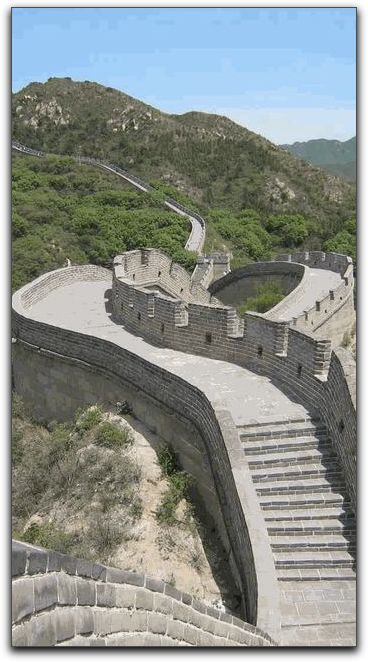瑞典学习圈传统的几点掠影 托瑞·波尔森 1973年, 我去北大西洋的一个岛国——冰 岛——旅游, 在那里我寄了一张我自己拍摄的照片 明星片给一位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新朋友。这 虽是一张仅写有几句话的简易明星片,但这几句话 我是用中文写的。 那个收到明星片的新朋友是我在汉语学习圈里的 老师。 去冰岛前的几个月,我和七八个其他参与者 一起加入了那个汉语学习圈, 而这位教师就是我们 这个学习圈的“学导”(学习圈的带领者)。 在1973年我们为何要开设这个汉语学习圈,其原 因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参加第二年夏天对任何瑞典人都 开放的首批去中国的旅行团。那个夏天之前,只有像 瑞典共产党领导人那样的一些特殊团队才能去中国。 而1973年这次,任何人都能够申请参加。当时就有 600多人申请,而最后审批下来的只有60人。 在我们这个学习圈里的成员有着不同的年龄和 背景。例如,其中有一个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待
过几年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儿子。另外一个是来自瑞 典极北部的气象学家——也就是从那时起,他成为 了我的一个最好朋友。最老的成员是一位年龄74岁 但心态很年轻的老船长。 我们的老师,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是一位 年轻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学生,他师从瑞典汉学家 马悦然教授(Göran Malmqvist)。马悦然在上个世 纪四十年代又是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的高徒——现在他在中国的名气要远远 大于在瑞典的名气。而如今,这个曾经的学生和学 习圈的“学导”也是一位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教授 和瑞典孔子学院的院长了。 我们在学习圈里很开心。我们每周聚一次,通 常在晚上下班后。我们经常在课后去咖啡馆,于 是那个74岁的老船长就喜欢开讲他全球航行时的故 事。我们也学习一些中文,足够让我们写一些简单 的明信片。 我们中的几个人还与学习圈的“学导”和他的一 些朋友一同成立了另外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圈, 学习现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我们读过的其中一本书叫 做《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这是伊莎贝尔
和戴维•柯鲁克在1959年合作撰写的。 学习圈简介 自加入1973年汉语学习圈之后,我们自然就承 袭了瑞典学习圈这一传统。 瑞典学习圈正式成立 于1902年。当时,奥斯卡•奥尔森(Oscar Olsson) 撰写、报道了瑞典第一个学习圈,并发展了关于学 习圈的观点和理论。由此,他被公认为“瑞典学习
圈之父”。 奥斯卡•奥尔森和陶行知、晏阳初一样,对教 育实践、教育理论和教育哲学方法都有探索。跟他 们一样,他也受到了美国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 奥斯卡•奥尔森的理想是: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自己 教育自己,跟朋友、同事、邻居组织起来一起学 习。他们不仅要共同分享各自在书中读到的东西, 还要分享各自的知识、经验和观点。学习圈中的参 加者在学习聚会期间都应该选择自己的阅读文献, 自己做些准备,与其他参与者进行积极的交流。学 习圈还是一个民主实践的论坛,参与者同时对学习 内容和学习方式负责。 奥斯卡•奥尔森认为,学习圈不仅仅是组织管 理学习的另一种形式:“一般而言,学习圈的目的 并不是聚积事实性的知识,而是培养和创造一种持 续探索、质疑的精神和学习气氛”。 20世纪,学习圈在瑞典越来越流行,对许多人 而言,学习圈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每学期或每年后他们再一起决定下一步要学习些 什么,同一组中的人们会在学习圈中持续学习许多
年,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通常,学习小组会形成 两个平行的学习圈,比如,一组学习农业或与其小组成员职业相关的一些科目,另一组学习文学或其 他类似的能满足他们心智或艺术修养需求的一些科 目。 许多学习圈也直接关注社区的发展。1950年之 前,在瑞典大约有2500个自治市和地方行政区,在 这些地方当局,总共有几万人是那些当地选举的代 表。这些代表中的许多没有高深的正规教育背景, 一些拥有学位,但是大多数人是工人和农民,他们 通常仅有六七年的学校教育。他们许多是从学习圈 中获得了一些主要的关于社会、经济、管理以及如 何参与地方政府活动等的理论和实践的教育。 学习圈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了议会成员、贸易联 盟的领导以及工会组织和政党的领导。假如你问他 们各自的政治生涯是怎么开始的,他们可能会说: “哦,是始于学习圈.....” 根植于非政府组织 学习圈的传统起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瑞 典发起的大众运动和组织。如:工会、各种政治组 织,禁酒社团组织,农民运动和其他各类组织。 瑞典当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大部分人生活在 农村。人均受教育水平很低,特别是工人和农民群
体。他们所在的组织意识到,为了提高其成员的利 益,要尽可能让他们能够学习,提高他们的知识水 平。这对于个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公民很重要。此 外,拥有受过教育的成员对于组织来说也很重要, 受过教育的人越多,组织就越强大。 那段时期是瑞典民主政治的奠基时期,是全体 公民政治权利得以充分保障的时期,也是选举权被 逐渐推广的时期。对每个人来说更多的政治权利也 意味着更多的政治责任——那也就增强了对更好的 教育和对社会更深层次的了解的需求。此外,为了 表达和发展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需要在组织内进 行相互合作。非政府组织和非正规成人教育成为了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奋斗的两股力量。 现代学习圈 多年以来,学习圈在瑞典建立了良好、坚实、 稳固的传统。学习圈在瑞典得以盛行的最重要原因 也许是来自国家和大多数地方社区的经济支持。从 1912年开始,瑞典政府决定对学习圈使用的各类书 籍给予资助。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学习圈也变得更受欢迎。 如今,瑞典900万人口中每年有近一百万人参 加学习圈。目前共有10个不同的组织负责安排全国 各地的学习圈,讲座和各种文化活动。 大多数学习协会属于非政府组织。举例来说, 最大的学习协会隶属于社会民主党、瑞典合作联 盟、几个贸易联盟和许多其他的工人运动组织。其 中一个最小的学习协会为穆斯林组织所有。 大众成人教育(Folkbildning) 10个学习协会是瑞典大众成人教育的一部分, 也称为瑞典非正规成人教育。大众成人教育的另一 部分由150家民众中学组成,我会在第三篇文章中 提及。 可以说,非正规成人教育是人们集体提升修养 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人们在充分知情,不同意见得
到尊重,并在理性思维的指导下进行的。“修养” 的概念包括广泛的通用知识,也包括成为一个负责 任的社会成员所需的其他素质。最重要的是要具有 能够将自己置于更广的范围内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日 常生活中看待事物的能力,如基于全球、历史、生 态的视野⋯⋯还包括具有健全的判断能力。最后, 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还要具有道德方面的素质, 即愿意按照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念和理解,采取与之 一致的行动。 大众成人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双重目的。一是成 为促进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的工具。另一个目 的是使个体参与者能够达成自己的梦想,实现自己
的抱负,发展自己的兴趣等。一开始,是以第一个 目标为主导的,现在第二个目标对于学习圈大多数 参与者来说更加重要。 “未来学研究”学习圈 1973年学中文的学习圈不是我参加的第一个学 习圈,而我的第一个学习圈是1968年关于未来学研 究,当时未来学在瑞典还是一个新概念。它始于 1968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一次公开会议,由斯德 哥尔摩大学的一群学生发起倡议。他们在全城散发 宣传单,邀请人们参加会议来了解更多的信息。我 很好奇,和其他上百个人一起去了那里。我们在会 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午夜分别之前,我们决定继
续在小组内进行讨论各种不同的子话题,这些小组也就是学习圈。 当晚,产生了约10个不同的学习圈。我们在一 个学习协会注册了我们的学习圈。然后,我们得到 了一些资助,够买一些需要的书籍。 在我的学习圈中,我们研究传播和媒体。我们 阅读的书目之一是加拿大学者和通信理论家马歇 尔•麦克卢汉(Marchall MacLuhan)的《媒体》。 他以其“媒体是信息”和“地球村”的观点而闻名 于世。你甚至可以说,他几乎在三十年前就已经预
言到了互联网的发明。 我们每次集中讨论上次见面时候确定的主题。 在此期间,我们阅读书中的章节。我们也在科学期 刊中寻找相关的文章,讨论新技术可能在未来带来 的影响。不过,我不记得有预言成真的。例如,组 中的两个成员在瑞典公司爱立信工作,但是他们并 没有预测到手机的发展。 其他“未来学”的学习圈关注环境问题,国际政 治,学校和教育,大学的未来等。好几次,所有的学 习圈都来进行共同讨论,就像第一次开大会那样。 “儿童和青春期心理学”学习圈 70年代初期,我在小学教师工会工作。那时我 感觉需要了解更多关于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方面的内 容,为此就这个主题注册了一个学习圈。共有40人 参加第一次会议,除我之外,其他39位都是女性,
均在日托所、幼儿园和小学工作。 由于人数太多,我们被分成了两个学习圈。我 很高兴每周与20名女性(19名参与者和学习圈的 “学导”)会面。 多年后,我成为了一个由我女儿班级的家长参 加的类似的学习圈的学导。我们每周在学校会面一 次,大部分时间都是家长在一起学习,少量时间家 庭教师也参与进来。我们阅读报纸、摘要和一些小 册子上的文章。这段时间内,我们一直将所读到的 内容与学校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 其中一本书是一位老师写的,题目为“要明确 立场并使之兑现”。这本书的主题思想是,为了成 为孩子模仿的典型,家长需要在道德方面坚定立场 并始终如一。例如,如果你时常抱怨那些撒谎和欺 骗别人之人,而你自己还贪赃舞弊、是个逃税者, 那么在你的孩子看来,你就不是真实、真诚的。 “盲人认识世界”学习圈 70年代初期,我作为一个旨在帮助世界各国 政治犯的所谓的大赦团体( Amnesty group)的成 员,多年来一直在道义上支持罗得西亚(如今的津 巴布韦)的一名政治犯,并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有关 非洲历史的学习圈。 在70年代,我还是一系列盲人学习圈的学
导——我们学习关于世界的主题。这个盲人团体的 成员中有老有少,他们都对了解这个世界有很大兴 趣。我们每学期都选择一个新的地域来学。从非洲 开始,接着是拉丁美洲,然后是印度,最后是中 国。这些参与者通过听磁带来“阅读”书本,这些 磁带是由瑞典盲人组织专门为盲人录制的(经费由 政府资助)。 每一个新学期开始之前,在介绍每个世界新地 域之前,我都会在一个大而薄的木板上制作一个简 单的地图,这块木板上我用胶水粘贴了各种各样的 布块和其他材料,以显示国界、高山、湖泊、河 流、大城市等等。塑料标签上用布莱叶盲文字母标
写出城市和地区的名字等。在每次上课集会之前, 我们都围着一个放置了这块木板地图的大桌子坐下 来,这样每个参与者都能通过他们的手指触摸“地 图”跟上我的讲解。每次我们都阅读和讨论一定的 主题:自然和地理、历史、经济、政治话题等。 “养蜂”学习圈 我还组织了几个关于瑞典北部高山的学习圈。 每到夏天就有人们去那里徒步旅行一周甚至更长 时间,带着帐篷、睡袋、食物等。在这样的学习 圈中,你要准备好学习关于动物和植物的生活、关 于方位知识、关于为了生存什么可以做和什么不能 做、需要带哪些器具等知识。 作为参与者,我参加的最让人兴奋的一个学习 圈是养蜂学习圈。这对我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在 那段时间内我能跟我的朋友们连续不断地谈论有关 蜜蜂的生活习性——如果他们允许我这么做的话。 之后我自己养了两三群蜜蜂,每个夏天我都能从它 们那里采到50-80公斤的蜂蜜。 关于“核能”的学习圈 在1980年瑞典有一次全国性的公民投票—— 公民在一次特殊的投票中选择支持或反对核能。这一公民投票缘于1979年美国三哩岛(Three Mile Island)核电站的核泄漏事故,那时瑞典政府的三 个政党关于瑞典核电站的前景意见不一致。瑞典已 经建有几个核电站,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该继续修 建更多或者⋯⋯ 在公民投票前的几个月内,瑞典就会有许多学习 圈讨论核能技术,关于它的优势和劣势,关于约数万 年存储和保护危险的放射性废料的风险等等。 当然,我也加入了这样一个学习圈。那时我住 在瑞典南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我们每周会面一 次,地点是在学习圈的学导家中,大家都围坐在他 家很大的案桌周围进行学习。 多年后,当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学习协会工作
时,我成为另一个关于核能的学习圈的学导。我们的 成员都是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为此我们常常在午饭时 间碰面, 快速的15分钟进餐之后讨论45分钟(一小时 午休)。我们讨论的议题之一就是如果有任何严重事 故,那么会发生什么。我们假设在瑞典第三大城市附 近发生严重事故,那么那里约有一百万人的整个区域 将被遗弃数年。 几个月后,1986年切尔诺贝利(Tjernobyl)的 核能发电厂发生了核溶解事故。 希伯来语的暗示 在学习圈中,我学习了包括中文在内的几门外 语。我曾开始学习俄语,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在一 段时间之后放弃了。这就是我只学习了头半部分西 里尔字母的原因⋯⋯ 大约十年以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瑞典我加
入了一个希伯来语学习圈——希伯来语是以色列主要 官方语言。我对这个学习圈的“学导”—— 一个以 色列女教师所使用的语言教学方法感到好奇。这种方 法叫做暗示感应教学法,是由一个保加利亚心理治疗 医师 Georgi Lozanov 发明的。暗示感应教学法的目的是 使用轻松的和古典的音乐来减弱感情阻碍因素对语言 学习的影响,以达到强化学习的目的。 在每次上课期间,我们交谈很多,并在一种有 特殊节奏的巴罗克音乐的背景下朗读课文。有一 次,大家还带来了食物作为晚餐。然而,我们并不 允许直接吃喝,除非我们使用希伯来语告诉某位同 学递给我们食物。如果使用的语句文法不对,就要
挨饿。 这是一个大约有八个参与者的有趣的群体。他 们中的一个希望去以色列探亲戚的时候能够讲一点 希伯来语。一名中年妇女想要参加下半年在耶路撒 冷举行的马拉松比赛。另一名大约20岁的妇女,正 好遇到了一个以色列的男青年⋯⋯(那时参加学习 圈最普遍的原因是为了爱情而学习外语)。 “犯人学习文学作品”学习圈 我作为学习圈的“学导”最近的体验是在二三 年前。我被人问及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学习圈的“学 导”,为一些在斯德哥尔摩北部的一个监狱里的犯 人开设学习文学作品的学习圈 。当然,这是很难
抵挡住的一次诱惑。 我有两个学习圈。参加者自愿加入,他们能够 在工作或者学习中选择。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宣称在 最开始从来就没有读过任何一本书。那是一次挑 战⋯⋯ 由于他们在文学作品学习方面并无经验,我们 决定读大量不同的短篇小说和小说节选。通过那种 方式,他们有可能发现一些愿意阅读的书。我们尝 试了部分现代小说,包括从北欧海盗时代开始的冰 岛古老传说,还有一些瑞典经典书籍,一些诗,还
有一些中国作家写的短篇故事。当然,我们也阅读 一两个犯罪故事中的部分内容。 在每次会面前,我发给大家一些文章段落来当 场阅读和讨论,另外一些文章让他们在下次见面之 前进行阅读。我也尽量让他们从监狱的图书馆挑选 自己喜欢的书。他们中的一个甚至挑到了经典希腊 史诗作品《奥德赛》。 不管怎样,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我也了 解了很多关于监狱里面的生活。每次我进入和走出
监狱,都必须走一遍搜身安全检查程序。一次,返 回家的路上我碰巧遇到了一个很久没见的朋友。 当他问我现在生活怎样,我说“我刚从监狱放出 来⋯⋯”,他怪怪地看着我⋯⋯ 还有去中国的旅行⋯⋯? 我曾经是几个其他学习圈例如学习中国、印度 和古巴的“学导”(在那时我们曾经到印度参观访 学,并在古巴援助劳动加旅游了一个夏天,当然还 没有去过中国)。我也曾经作为参与者参加了几 个学习圈,例如桑巴(一种巴西舞蹈)。最近我参加的一个学习圈是在去年,学习政治哲学。我们 进行了大量有趣的讨论,例如关于现代世界的道 德问题,关于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米歇尔•福柯(Michael Faucault)、罗 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等名人的作品。我 们讨论权利和自由、平等和民主、国家和暴力等主 题。 那么,我在文章前面提到的1973年的汉语学习 圈里那些人(申请参加去中国的旅游团)后来结局 如何?我自己并没有能够成为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 去参观中国的幸运儿。然而,74岁的老船长是幸运 的。他到了中国,甚至还尝试使用了他那有限的几 句中国话。我还记得看过一张他和另一位74岁的中 国老农一起坐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照片。那位来 自瑞典北部的气象学家——我的好朋友也幸运地成 为了那个去中国旅游团中的一员。 2015-10-29 © Tore Persson Comments to: tore.persson@folkbildning.net |